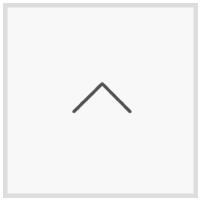致,青春 -- 2016極地馬拉松內蒙站
這次參加內蒙超跑的感想,用了一個星期,終於寫完這8000字的文章。
過程中有太多要感謝的人了,讓我一一道來:
鄭仁凱, Sam Eng Sun,沒有你們兩個人的陪伴,我真的沒辦法想像我要怎麼完成這次的賽事。明年新疆見。
Angus Lok,我不會忘記你在賽前一天跟我說你好緊張,大家看起來都好厲害,然後你就跑第三名的事。實在是不可原諒。
李霽 (Joshua Lee), 因為你,讓我真的下定決心買了Fenix 3, 還刷我老婆的卡.......
周青, 柯建銘 (Oscar Ko), 江俊宏, 呂胡忠, 煜錩彭, Lee Keng Fatt, 可以認識你們是我的榮幸,賽道上一定可以再見面的。
Swim Yo, Yu Xin Zhou, 辛苦的工作人員,只要是你們辦的活動,我都十分的放心。
林義傑大哥,只要你繼續推廣超馬賽事,我就會繼續參加下去。
最後,謝謝我老婆 葉雨青,可以容許我的任性,還有滿足我這個近中年男子的購物慾!
謝謝大家。
我在這裡也放上一些我文章中提到的歌的連結,有空可以聽聽看這些影響我一輩子的音樂。
Wish You Were He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dNnw99-Ic
Real Lov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7krBKzmVI
這篇文章裡提到蠻多死亡的意象的,絕對不是說這個活動本身具有多大的危險性(其實主辦單位很棒的),而是我自己認為,只有對死亡這個議題思考的越深,越能體會活著的意義。
致,青春 -- 2016極地馬拉松內蒙站
所以,這篇文章並不專注在寫賽道的景色以及我如何用堅忍的意志一天又一天的來完成這場111公里的沙漠超馬。比較想說的,是透過賽事的過程,審視著自己的一切。出現在我腦中的,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在我生命中出現過的某些人,也可能是我在沙漠裡面胡思亂想出來的一些東西。當然,每個人想的可能是不同的歌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但只要能夠稍稍得到一些共鳴,讓其中的一些人也能回想起一些自己以為自己早以遺忘的事,也就夠了。
「致,青春」是在參賽過程中的一台補給車車體上印的充滿現代感的字,由當地的司機大哥駕駛,載著工作人員以及補給用的水,停在一些補給點上,等待著每個參賽選手。我常常看著它停在遠方的一個點,讓我知道我又完成了一個關卡。到那兒稍事休息,補完水,繼續出發後不久,又可以看到這輛車從我身旁呼嘯而過,然後越過遠處的沙丘,消失在我的視線當中。我很喜歡這種努力追尋著青春,然後在不知不覺中,青春又倏然消逝不見的帶點超現實的感覺,所以用此作為標題。
------------------------------------------------------------------------------------------------------
如果要我說一個同時描述希望與絕望的故事,可能會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在沙漠中跟自己的同伴失散了。而幾個小時前,他喝完了身上的最後一滴水。他所有視線的空間,只有交會在遠方地平線的黃色的沙和藍色的天空。四周沒有足以帶給他任何希望的桅杆。
直到越過了這個山丘。
他突然發現在一旁的山丘,有另一對腳印。他連忙跟了上去,想說或許有機會得救,雖然在這個無風的天氣,那對腳印可能是幾個或幾十個小時之前留下的,但那畢竟是一線希望,儘管細若游絲。
直到他越過了那一座山丘,在腳印結束的盡頭,他發現了他同伴匍匐趴倒的地上的身影。
而在失散之前,他保管著他與他同伴,兩個人的水壺。

我現在就正行走在內蒙的沙漠中。三天,總距離111公里。
這時候已經是正午十二時左右,氣溫大約是攝氏四十度,我幾乎感覺不到任何汗滴從我皮膚表面滲出,但是卻可以清楚的知道陽光正無情且貪婪地吸允著我身上所有的水分,從今早的七點半起跑的時間開始。第一天的路程表定是38公里,但因為沙漠的地貌隨時在改變,誰也說不準到底實際距離是多少。沙地很軟,自己的雙腳每踏出一步,沙子都會將我的腳掌給吞沒,我必須多花許多力氣將自己的腳從沙漠的口中掙脫出來,然後繼續前進,就這樣不停不停地重複著。
一般說來,每十公里就會有一個補給站,約莫走兩個小時就能到達。然而今天的第二個補給站與第三個補給站間的距離特別長,剛才在第一個補給站裝滿3.5公升的水,走了兩個半小時,已經被我喝完了。而補給車的影子,卻還沒出現在視線當中。
「那麼,」我這樣的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到這個地方來?」
我不知道在哪兒曾經聽過一段話說,身為理性動物的重大優勢,在於能為自己的任何行為找到理由。如果真是這樣,我可以為我想來這個名叫烏蘭布和沙漠的念頭,找到任何的理由嗎?
烏蘭布和沙漠位於內蒙烏海市旁,在蒙古語來說,烏蘭布和指的是「紅色公牛」。據當地人的說法,這是因為地層中焦煤這個礦產十分豐富,當陽光照在沙漠上的時候,呈現出赭紅的顏色,所以才這樣稱呼它。烏海從以前就以採礦及重工業為主要的經濟活動,但時至今日,因為過度的開採,使得煤礦資源日益枯竭,陸陸續續的一些企業逐漸出走。
我右手邊的兩座沙丘之間,可以看見遠方有一個仍在運作的採礦場。灰黑色的大卡車在一個漆黑的山洞中進進出出,從這頭沈睡的紅色公牛體內,像是要掏空祂的內臟般開採出一車車的煤礦,即使也意識到這頭公牛的生命正逐漸地消逝,卻仍然在牠體內架起一根根支撐牠枯槁的身體的支架,繼續刨挖著他所剩下的一切。或許要等到某一天牠頹然塌陷,不用再繼續餵養著貪婪的人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靜。
這時候太陽當頭掛著,我的影子怯生生的所在我腳下。雲似乎也受不了這樣的溫度,一起消失在湛藍的天空當中。我的口乾舌燥,卻又沒有任何水喝。剛才從第一個補給站出來之前,我才看到地上有隻蜥蜴張開四肢仰著頭,就這樣因為缺水被曬成乾,而我現在開始想著自己的命運會不會跟那隻蜥蜴一樣。
似乎好像有一首歌多多少少描述出這樣的畫面,我於是停下腳步,戴上耳機,把iPod選到Pink Floyd那一欄。在一段用五聲音階演奏的經典吉他前奏後,Roger Waters(在此刻有些黑色幽默的名字)帶點沙啞卻又清晰的聲音開始這樣唱著:

Pink Floyd在1975年發表這首“Wish You Were Here”,收錄在同名專輯裡面,用來獻給前主唱Syd Barrett。Syd因為精神上面的疾病以及受不了成名後的壓力,將自己與迷幻藥劃上等號,除了不停在精神病院進進出出,表演時更常常愣在舞台上,不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就是亂彈一些根本不對調子的吉他聲響,逼得其他團員們必須收拾爛攤子。在1968年一次巡演,考量到數以萬計的歌迷以及龐大的經紀約,團員們很有默契的一起「忘記」去接Syd,之後,Syd就正式被除名了。接下來的日子裡,樂團沒有人跟他聯繫,沒有人知道他在哪,但彼此卻都心知肚明的背負著對Syd內疚與矛盾的心情。終於在1975年的這張“Wish you were here”的同名專輯中,他們坦白地面對自己脆弱的情感,歌曲除了描述著當代人迷失在工業化那一切講求效率的冷冰冰的世界,更希望的是Syd也能跟他們同在,對抗這個無以名狀的巨大陰影。這張專輯跟Pink Floyd在70年代所有的專輯一樣,取得了莫大的成功。
而Syd之後呢?除了一些斷斷續續的音樂活動之外,再也沒有任何足以在音樂圈稱道的事。1974年在Abbey Road Studio雜亂的做完最後一次錄音,他就從音樂圈徹底地消失了。1975年6月5日,當Pink Floyd的團員們進行這張專輯的錄音時,看到有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錄音室後方。那個人身形十分臃腫,穿著十分邋遢。他剃光了自己所有的頭髮跟眉毛,有時候會自顧自地站起來,用手指甲刮著自己的牙齒,然後瘋瘋癲癲的跳來跳去。團員們問在場的工作人員說那個人是誰,當聽到是Syd的時候,全部的人都哭了。
儘管如此,Syd不曾在之後的任何一場Pink Floyd的演出中出現,他就這樣繼續消失了三十一年,然後在2006年時,死於劍橋的家中。死亡證明書上,他的職業是「已退休的音樂家」。
Syd,得年60歲。
然而,對絕大部分的人來說,他早在29歲的時候死去,然後在60歲的時候被埋葬。

遠方的沙丘頂端出現了補給車的影子,我跟兩位同行的選手們卻也沒辦法加快腳步,還是只能一步步慢慢的走向補給站。嘴裡早已經沒有唾液可以潤濕我的嘴唇,我想已經裂開一陣子了,用舌頭去舔的時候,隱隱約約可以嚐到血絲那鹹鹹甜甜的味道。工作人員小小的身影在遠方用力的揮手,大聲幫我們加油,我知道我就算在這裡倒下去,也終於能夠得救了。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在補給站補完水,稍微休息個十分鐘後,繼續出發往終點前進。離第一天的終點剩下不到十公里,我回過頭看看自己已經走過的路,越過的沙丘,「在那兒有花開,棲息著蟲子跟禽獸。那是利用強韌的適應能力,逃到競爭圈之外的生物」,安部公房這麼說著。我試著從資本主義建構出的異質化的世界中逃到這裡,還不知道我在什麼時間點已經或是將會真正的死去,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現在還不想被埋葬。
第一天的營地位於兩個沙丘之間較為平坦的沙地上,下午六點多,我跟其他兩位同伴們走到了。許多提早到的其他選手們,在沙丘上坐著休息拍照,我沒有這樣多餘的力氣。只趕快找到自己的帳篷,換上輕便的衣服,拿出背包裡的乾燥飯,到營地的休息區要了熱水,三兩口把它吃完以後,肚子仍然沒有被填飽的感覺,於是再從背包裡拿出一包泡麵,也不管第二天的糧食到底夠不夠。

傍晚七點多的時候,太陽仍然固執的在地平線上方徘徊著,卻也漸漸地失去了原先的熱度。慢慢的有些風從沙丘的頂端往我們這兒吹,感覺起來是老天在我們一天的辛勞之後,給我們的些許恩賜。有些選手也在附近坐著休息,我們聊著今天走過的路,一起吃著晚餐,享受著這片刻的美好。
我跟身旁的人說了:「其實仔細想想,人要的真的不多。」
「是啊,好像真是這樣。」他笑著回答我。
但是,我們到底要什麼呢?
我唸高中的時候,班上有一位同學,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一直讓班上永遠的第二名恨得牙癢癢的。他的個性外向活潑,對每個人都十分客氣。我們常一起打籃球,一起天南地北的聊。那時候沒有手機,沒有筆記型電腦,更沒有現在存在或是已經被淘汰的一些所謂的社交軟體,所以很多事情還不顯得太過於虛假。
「台大醫科就是我的第一也是唯一的志願。」他常這樣說。事實上我也覺得他可以輕鬆做到。「不過在那之前,我一定要在畢業舞會上跟同一個補習班的那個女生告白!」好吧,這一點我就懷疑他做不做得到了。
畢業舞會前二個星期的某一天,他沒有來上課,老師說他因為流感身體不適,昨晚去醫院吊個點滴,看情況應該過不久就可以出院了。幾天以後,老師再說,因為一直沒好,現在換個大醫院看看。我跟同學想說下星期就是畢業舞會了,而且告白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他就算爬也會從醫院裡面爬出來。
舞會當晚,他沒到,不過補習班的那個女生到了。「馬的,你真那麼沒種嗎?」我心裡這樣想。
音樂響起的時候,同班的另一位朋友走過來跟我說:
「他死了。」
「幹,這種事情可以拿來開玩笑的喔!」
「淋巴癌。」
我朋友面著光,鹵素燈把他的臉色照得慘白,只剩下泛著淚的雙眼跟被他咬的腫脹而顫抖的下唇,露出深紅的血色,突兀的存在他此時因為燈光照射而顯得過於平版的臉上,帶點可悲的可笑。然後他一直看著我,沒有說話。
對於那個畢業舞會,我剩下的記憶是,那位補習班的女孩子,在跟我們班上的另一位同學說完話以後,摀著臉從我們校門口跑出去。
事後,我才知道,他為了自己那個第一也是唯一的志願,每天晚上唸書到凌晨兩點多,早上又六點多就起床,身體因而過度勞累,但自己卻沒有發現。而本來以為是感冒的症狀,其實已經是淋巴癌的末期了。直到一開始去住院的診所發現不對勁,要他到大醫院去檢查後,才發現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不到一個星期,就因為器官衰竭結束了他短暫的人生。他母親跟我們說,他在病床上,小小聲的說出他最後一個願望:
「我想跟同學一起參加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當天,我們把原本應該是屬於他的位置空了下來,擺在上頭的,是那位補習班女孩送來的一束花。
「恭喜你,終於畢業了。」花上的卡片寫著這幾個字。
九點多天黑了,我從帳篷走出來,即使白天有著四十度的高溫,現在沙漠裡也只剩下十五度左右。我加了一件薄外套,去營站拿張板凳,到一旁沒有光的地方,點根菸。菸頭那紅色的火光,照不開我面前的褐黃色的沙。
沙漠裡沒有光害,月亮像是用眉筆小心翼翼地把沙丘的稜線勾勒出了銀白的色彩。銀河如薄紗般,安靜且溫柔的環在廣袤的天空。偶爾吹來的風,輕撫著這個熟睡的世界。北極星幾十億年一直安穩的掛在大熊星座斗勺的上方,為迷途的人指引著方向。
過了19年以後,我的那位高中同學,仍舊以18歲的樣子活在我的心中,而我已經逐漸老去。
「嘿!你還記得我們以前一起聽的Beatles嗎?」當天晚上他出現在我夢裡,問了我這句話。
「我想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我說。
「那我們一起來唱一段吧。」
「好啊。」

------------------------------------------------------------------------------------------------------
「因為你注定要到這個地方來。」
一位負責將指引參賽選手道路的小紅旗回收的工作人員這麼跟我說:「一定是你前輩子跟這塊地有些淵源,許多緣分還沒還清,所以你這輩子還要到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這會是我問題的答案嗎?
第二天的路程有五十多公里,一早沒什麼太陽,取而代之的是夾雜著地上細微砂粒不斷吹起的強風,從我的耳邊快速地刮過。天空的雲層很厚,像是久未整理而顯得糾結雜亂的羊毛般,隨著風努力拖著自己看似笨動的身軀,卻快速地移動著。風沙遮蔽我的視線,也淡化了四周景物的色彩,一切的一切慢慢的融進黃褐色的背景當中。我把Buff領巾拉上,罩住我的口鼻,抬頭看著前方的路。今天路程中有許多沙丘特別陡,遠遠的只看得見如米粒大小般的小紅旗,在被越堆越高的沙給掩埋的同時,努力地想探出頭喘口氣。先前的選手們留下的足跡,幾十分鐘內就會給不停流動的風弭平,彷彿在嘲笑任何試圖在沙漠中留下存在的印記的事物。
「我把這一切都Reset過了。」沙漠這樣說道。
「但我踏在妳身上的每一步,我還是希望可以留下一些曾經存在的證明。」我說。
「你不過只是另一個薛西佛斯罷了。」
然後我的耳朵只留下了空洞的風的聲音。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每次參加這種極地馬拉松賽事,與其美其名的說我在追尋些什麼,不如說我是在逃避些什麼。我對於我的人生並沒有什麼太多不滿的地方,有份工作,有個小家庭,銀行也有些存款。偶爾抽抽煙,跟朋友喝點小酒,雖然並不是一個足以拿出來炫耀的人生表率,卻也沒有太多可以挑惕的。成長這件事帶給我最大的改變,是認識一隻叫做「現實」的獸。牠沒有固定的形體以及顏色,就算有,似乎也沒有人留意過。祂平時只縮在一個陰暗角落裡,無聲無息的張大嘴,等待著人們丟棄一種被稱為「夢想」的東西,作為祂的糧食。祂有時會看到有人大力地流著眼淚將自己的夢想送進祂的嘴裡,不過大部分時候,人們的夢想是不知不覺的從他們自己黑色西裝口袋中掉了出來,祂只需要守在人們每次酒酣耳熱應酬後的燈火闌珊處,然後就能夠咀嚼著關於夢想的酸甜苦辣以及歡喜悲傷。
我告訴我自己說,「我的人生,這樣就好。」
Roger Waters 接續著昨天的歌,在我的耳邊繼續這樣唱著:

我的那位高中同學還來不及面對社會的現實,就帶著夢想從現實的生活遠去。對於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們的故事,我想這樣跟他說:
「嘿!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是這樣過日子的:我們穿著西裝打著領帶,被丟進了生活的魚缸中,日復一日的囚泳在其中。魚缸四周玻璃壁被放上鏡子,除了讓身處其中的人們欣賞自己光鮮亮麗的外表外,同時也製造出這是一個廣大的世界的假象。有時候,當我們以為找到一個可以與自己一同前進的夥伴,卻總在轉過身後,才發現那其實不過只是自己的另一個倒影罷了。然而,我聽說過魚的記憶力只有七秒,這會不會是說,在每次的轉身,我們就會忘記我們是在一個魚缸裡,跟自己的倒影說話,這一個可悲的事實。但也是因為我們有忘記的能力,所以才有快樂的存在。」
遠藤賢知在「20世紀少年」這部漫畫的前幾集,也一直告訴自己:「我的人生,這樣就好。」。然後過不了多久,他就轉身對抗想要用病毒毀滅全世界的敵人「朋友」,並留下一句帥到不行的話:
「每一個人,總會有非去幹一次不可的時候。」
所以,感覺上,我並不是因為追尋著某種生命中的「注定」而來到這個地方,而是因為想要逃離以另一種既定形式存在於生活中的「必然」,所以現在我頂著風,走在一個又一個沙丘的稜線上。我左右手的手背,因為連續兩天的曝曬,除了發紅之外,已經有嚴重的刺痛感,但我不斷地一步步往前踏,這是我唯一可以更接近終點的方法。有時候感到疲倦,我跟同伴會坐在沙丘的頂端歇一會,回頭看著我們來時留下的腳印,被沙漠裡吹拂的一陣陣的風,輕輕地弭平曾經存在的痕跡。
我們三個人輪流領頭,使得後方的人可以踩著前方的人留下的腳印行走,可以稍微地省些力氣。已經走了五十多公里,花了將近十三個小時。風勢現在變得比較小了,偶爾可以看到太陽從西方的沙丘頭上探出頭來。
將近七點半的時候,天色轉暗,因為安全上的顧慮,主辦單位開著沙漠用的吉普車,準備把還沒完成賽事的選手們接回營地。當地人這樣跟我說,即使他們從小在這個地方成長,現在幾乎每天都開著車進沙漠,但是,唯一不能觸犯的禁忌,就是天黑以後,還留在沙漠裡。我聽說過當討海人學會感到對海洋的恐懼之後,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漁夫。對於生活在這兒的人們,那令人感到敬畏的神祉們,存在於沙漠當中。那些神祉們或許時常對人們抱著寬容且慈愛的心,但仍有屬於他們自己那神聖不可侵犯的時間與空間。
不過現在還有光,我們距離今天的營站大約只剩下ㄧ、二公里,不論如何,我們都要在關門時間內完成今天的路程。都已經走到這個地方了,繼續下去早已經變得比放棄容易多了。太陽此時快西沈,陽光將我的身影拉的很長,消失在肉眼看不到的遠方。現在帶著太陽眼鏡已經看不清楚小紅旗了,於是我把眼鏡脫下來,用著天空微光,想要看清楚最後的路途,卻一直看不到第二天終點的營站。我們低著頭,快步的向前走,直到工作人員把我們叫住,指著停在一旁的廂型車,說因為今天沙漠的風沙太大,無法紮營,要我們上那輛車,今天晚上的住宿點改成當地酒莊的蒙古包。我們一直不確定這代表我們今天完賽了,還是超過了今天大會的表訂時間而被迫棄賽,直到大會的裁判長再三跟我們確定我們完成了今天的賽事,我跟同伴們抱在一起,興奮的大叫。
我已經記不得上一次因為自己達成某種成就而感到如此興奮是甚麼時候了,但當下我知道,我還保有對生命的熱情。
約莫二十分鐘的車程,我們到了今天晚上住宿的酒莊,還來不及換下身上沾滿沙塵的服裝,就被指引到餐廳去吃晚餐。酒莊的人非常熱情,除了當天下午宰了兩頭羊作為選手跟工作人員的菜色之外,更拿出自家莊園釀的紅酒招待大家。敬過一輪又一輪後,我走出用蒙古包搭成的餐廳,在一旁找了一個角落,蹲在地上吐了起來。
餐廳內仍舊喧鬧異常,我清了清嘴巴,站起身,點了根煙,想要淡掉那遺留在食道內胃酸及葡萄酒混合的味道。天空中的星星以及不遠處已經可以清楚辨識的都市燈火,閃著朦朧的光芒互相呼應著。許多日子以來,只出現在歷史與地理課本中的黃河,現在就在前方流淌著。她滾著時間的巨輪,在一個又一個的朝代裡看著依附著自己而存在的城市們,從日出到日落,從興起到衰頹,不斷改變著他們的樣態。唯一不變的,只有天空中閃爍著藍白光芒的北極星,靜靜地看著這條孕育著生命的母親河。
於是,這個晚上,時間在該沈默的地方,悄悄的沈沒了。
------------------------------------------------------------------------------------------------------

最後一天的路程只有二十多公里,基本上是跟同伴們一起說說笑笑完成的。這次除了左腳腳掌因為鞋子進沙摩擦的關係,起了三個小水泡,其他沒甚麼不適的地方。終點前五公里,我們轉進最後一段的沙漠區,在越過這趟旅程的最後一個沙丘後,終點站所在的建築就出現在視線中了。我回頭看看這個整整待了兩天的沙漠,美麗的起伏如同女人身體柔軟的曲線,在湛藍的天空下慵懶的躺著。
快到終點的時候,不論是工作人員或是已經完賽的選手,每個人臉上都堆著笑容,一一的與我們擊掌擁抱。我先到了代表著完賽的地方,但不急著越過那條線,這三天與我一起走過這些路途的同伴們,我們一定要一起進終點。
於是三天111公里,結束了。
我們一群互不相識的人們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一個原本這輩子沒想過會造訪的地方,分享著自己的人生,之後再一一散去。大家在慶功宴上彼此交換著自己的聯絡方式,但我們彼此都清楚,有些人還會出現在下一個賽事中,而有些人這輩子可能沒有機會再見面,不過,我們很盡興且滿足地享受著當下,這也是每個超馬賽事後,最值得珍惜的時光。
------------------------------------------------------------------------------------------------------
最後一天的凌晨四點,一行人坐在往機場的小巴上。有人低著頭滑手機,有人繼續沈沈地睡去。我看著窗外,米黃的車燈打在路旁小幅隆起的沙丘上,把立體感從我所知覺的空間剝除,有點像是被裁切過的褐色瓦愣紙平貼在黑色的背景布幕上,從車窗的方框快速地閃過一幅又一幅的畫面。透明的玻璃分隔出了兩個不同世界,我處在一個小型密閉空間的這一端,有恆溫的空調系統,有舒適的黑色皮座椅,有現在正小聲地播放時下流行歌曲的音響設備。另一端的世界,現在或許仍舊刮著風,或許有許多夜行性的小動物躡手躡腳的覓食著,也或許那些沙漠中的神祉們,現在仍然安靜的悠悠沉睡著。
十二個小時以後,我會重新回到我出發的地方,繼續著我原來的生活。
突然間,我對於「我為什麼來到這裡?」這個我在沙漠裡的這幾天一直不斷問自己的問題,有了一個最真實的答案,而這個答案,竟是如此的簡單與純粹:
「因為我還活著。」
也因為如此,我才來到這裡。而我也知道,只要我還在賽道上,大家終會有相遇的一天。
所以,我想對那些所有認識我的不認識我的,我認識的我不認識的,現在的以及未來的朋友們,誠摯的說一聲:
Wish You Were Here.

本文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文章仅代表作者看法,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有不同见解,原创频道欢迎您来分享。来源:爱燃烧 — http://iranshao.com/diaries/193920